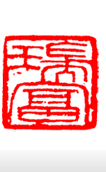|
从陈永洲案看侦查机关案情公布
2013年10月18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刑事拘留。2013年10月26日,央视《朝闻天下》节目中,陈永洲面向镜头承认收受“50万元”。2014年10月17日,湖南长沙岳麓区人民法院对陈永洲案公开宣判,查明陈永洲于2013年5月28日收受他人3万元。 这47万的受贿款差价去哪儿了?与怀疑长沙警方留下了相比,笔者更愿意相信长沙警方当初公布的案情信息是错误的。个别不自重的媒体无视基本法治原则做倾向性报道,当然应当谴责,但追本溯源,更应当审视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案情公布活动。 矛和盾都掌握在侦查机关手里 侦查信息是秘密吗?根据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公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正在侦察、预审的刑事案件的具体方案、重要案情和侦察、预审工作情况”属于秘密。 公安机关披露侦查信息违法吗?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事件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所以,公安机关披露案件信息至少是有章可循的。 犯罪嫌疑身陷囹圄,除了侦查机关同意外,恐怕没有媒体能进入采访辩解;侦查信息属于秘密,此阶段唯一可担任辩护人的律师,即使知晓了不同的信息也不得披露。相反,侦查机关则既要保密又得披露,虽是手持矛盾两头忙,倒也运用自如。现状就是:侦查机关公布的案情信息,都是无法辩驳也无人辩驳的,案情的公布即完成了对案件的舆论定性和新闻审判。 侦查机关公布的案情信息未必都对 案情信息出自侦查机关,看似权威准确,无可辩驳,但司法案件中抓错了人、判错了案绝非不可能,所以制度设计才有了分工负责,有了一审、二审、再审、甚至……信访。皮尚且如此,毛当然也不能例外。 长沙警方当时披露给央视的陈永洲案“重要案情”:有“数十万”、陈永洲面对镜头承供的“50万”和现在法院一审认定的3万,只能说,这一前一后搞的都挺哗然的……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永洲构成犯罪,有无二审及判决是否最终生效还有待观察。这决非个案,事实上侦查机关披露的信息不靠谱者常有,其中集大成者,当属已广为人知的“律师李庄伪证案”…… 即使案情公布错了也无须承担责任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十大信息公开案例”——“奚明强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相关负责人点评认为:“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双重职能,其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时制作的信息不属于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有点儿乱,我们还是整理下吧: 1、侦查机关公布的刑事侦查活动中掌握的相关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2、案情公布是侦查机关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3、公民不能认为侦查机关公布案情信息的行为侵犯其权益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4、侦查机关公开的涉及个案的信息内容不能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进行,要查阅了解,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5、目前的《国家赔偿法》中并无单独的“名誉权”、“荣誉权”的赔偿规定。 综上,面对侦查机关发布的相关案情信息,哪怕是存在明显错误,甚至是抹黑,除非是案件最终被认定是错案,当事人可就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事项申请国家赔偿外,其他救济渠道,无! 期待案情公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刑事诉讼活动不仅只涉及人身自由权、身体健康权,也关乎涉案个人的“名誉权”、“荣誉权”。侦查只是个开始,是否成立,仍须研判,处在涉密阶段的侦查机关,应该谨慎对待个案的案情公布。若调子都定好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还如何能实现呢? 再看《新快报》当年的“请放人”、“再请放人”报道,时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都在期待和关注着改革。转眼,已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了,“依法治国”成了主题,我们期待着符合法治理念的一切变革。
|